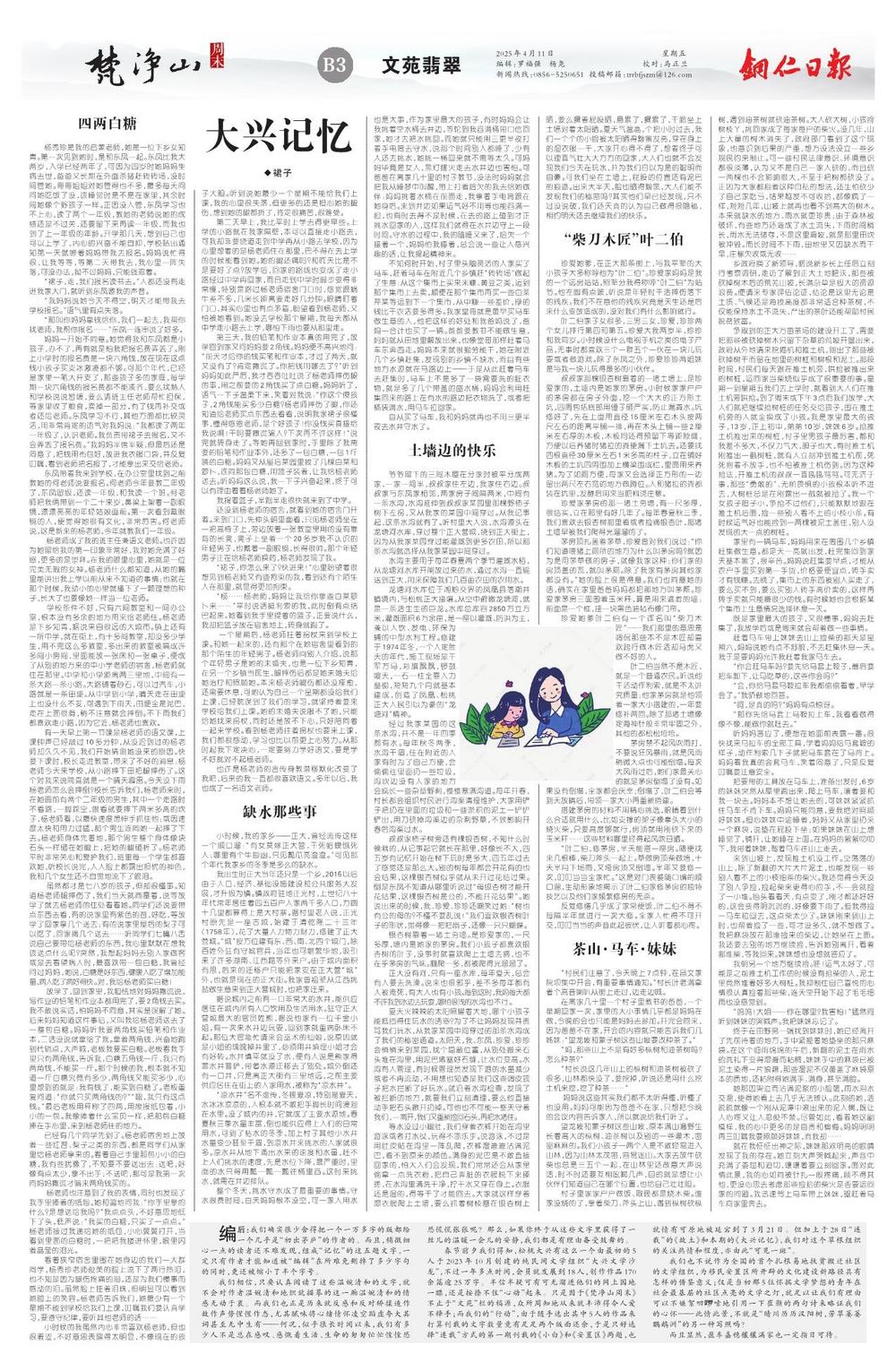四两白糖
杨秀珍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是一位下乡女知青。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和东凤一起。东凤比我大两岁,入学已经两年了,可因为四岁时她妈妈生病去世,爸爸又长期在外面杀猪赶转转场,没时间管她。哥哥姐姐对她管得也不多,最多每天问问她吃饭了没,该睡觉时是不是在家里,其余时间她像个野孩子一样。正因没人管,东凤学习也不上心,读了两个一年级,教她的老师说她的成绩还是不过关,还要留下来再读一年级,而我也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开学那几天,想到自己也可以上学了,内心的兴奋不能自抑,学校贴出通知第一天就缠着妈妈带我去报名。妈妈说忙得很,让我等等,等第二天带我去,我心里一阵失落,可没办法,拗不过妈妈,只能强忍着。
“裙子,走,我们报名读书去。”人都还没有走进我家大门,就听到东凤邀我的声音。
“我妈妈说她今天不得空,明天才能带我去学校报名。”语气里有点失落。
“那叫你妈妈拿钱给你,我们一起去,我帮你找老师,我帮你报名……”东凤一连串说了好多。
妈妈一开始不同意。她觉得我和东凤都是小孩子,办不了,再有就是怕我把报名费弄丢了。刚上小学时的报名费是一块六角钱,放在现在这点钱小孩子买支冰激凌都不够。可那个年代,已经是家里一笔大开支了,那些孩子多的家庭,每学期一块六角钱的报名费都不能凑齐,要么找熟人和学校说说暂缓,要么请班主任老师帮忙担保,等家里收了粮食,卖掉一部分,有了钱再补交或者还给老师。东凤学习不行,其他方面都比较灵活,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妈说:“我都读了两年一年级了,认识老师。我负责带裙子去报名,又不会弄丢了报名费。”我妈妈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把钱用布包好,放进我衣服口袋,并反复叮嘱,看到老师把名报了,才能拿出来交给老师。
东凤带着我来到学校,在办公室里找到之前教她的何老师说要报名。何老师今年要教二年级了,东凤留级,还读一年级,和我读一个班。何老师把我俩带到一个二十来岁,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漂漂亮亮的年轻姑娘面前。第一次看到戴眼镜的人,便觉得她很有文化,非常厉害。何老师说,这是新来的杨老师,今年就教我们一年级。
杨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许因为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我对她充满了好感,更多的是崇拜。在我的眼里心里,她就是一位完美无瑕的女神。杨老师什么都知道,从她的嘴里能讲出我上学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幼小的心里就播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长大了也要像她一样当一位老师。
学校条件不好,只有六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方用来给老师住。杨老师是下乡知青,据说来自很远的大城市。镇上还有一所中学,就在街上,有十多间教室,却没多少学生,用不完这么多教室,多出来的教室被隔成许多间小房间,里面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便成了从别的地方来的中小学老师的宿舍,杨老师就住在那里。中学和小学距离两三里地,中间有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大路铺着砂石,可以过汽车,小路就是一条田埂。从中学到小学,晴天走在田埂上也没什么不妥,可遇到下雨天,田埂全是泥巴,走在上面很滑,稍不注意就会摔倒。不下雨我们都喜欢走小路,因为它近,杨老师也喜欢。
有一天早上第一节课是杨老师的语文课,上课钟声已经敲过10多分钟,从没迟到过的杨老师却久久不见,我们开始猜测她没来的原因。快要下课时,校长走进教室,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杨老师今天来学校,从小路摔下田把腿摔伤了。这个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今天没下雨杨老师怎么会摔倒?校长告诉我们,杨老师来时,在她面前有两个二年级的男生,其中一个走路时不看路,一脚踩空,眼看就要摔下两米多高的坎子,杨老师看,以最快速度想伸手抓住他;或因速度太快和用力过猛,那个男生连同她一起摔了下去。杨老师身体先着地,那个男生整个身体像块石头一样砸在她腿上,把她的腿砸折了。杨老师平时非常关心和爱护我们,班里每一个学生都喜欢她,听校长说完,人人脸上都露出担忧的神色,我和几个女生还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虽然都才是七八岁的孩子,但却很懂事。知道杨老师腿摔伤了,我们当天就商量着,说等放学了就去杨老师的住处看看她。同学们还说要带点东西去看,有的说家里有紫色的苕,好吃,等放学了回家拿几个送去;有的说家里屋后的梨子可以吃了,回家摘几个送去……听同学们七嘴八舌说自己要带给杨老师的东西,我心里默默在想我该送点什么呢?突然,我想起妈妈去别人家做客或是去看望病人时,最喜欢带一包白糖,我曾经问过妈妈,她说,白糖是好东西,健康人吃了增加能量,病人吃了病好得快。对,我给杨老师买白糖!
放学了,回到家里,我胆怯地对妈妈撒谎说,写作业的铅笔和作业本都用完了,要2角钱去买。我不敢说实话,怕妈妈不同意,其实是误解了她。后来妈妈知道这件事后,又叫我给杨老师送去了一整包白糖。妈妈听我要两角钱买铅笔和作业本,二话没说就拿给了我。拿着两角钱,兴奋地跑到代销点,大声喊,老板我要买白糖。老板看我手里只有两角钱,告诉我,白糖五角钱一斤,我只有两角钱,不能买一斤。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一斤白糖究竟有多少,两角钱又能买多少,心里想到的就是:我有钱了,能买到白糖了。老板重复问道:“你就只买两角钱的?”“嗯,我只有这点钱。”最后老板用秤称了四两,用废报纸包着,小小的一包。我像捧着什么宝贝一样,把那包白糖捧在手心里,来到杨老师住的地方。
已经有几个同学先到了。杨老师宿舍地上放着一些红苕、梨子之类的东西,都是同学们从家里给杨老师拿来的。看着自己手里那包小小的白糖,我有些犹豫了,不知要不要送出去:送吧,好像有点太少,拿不出手;不送吧,那可是我第一次向妈妈撒谎才骗来两角钱买的。
杨老师也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同时也发现了我手里捧着的纸包。她和蔼地问我:“你手里拿的什么?是想送给我吗?”我点点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低声说:“我买的白糖,只买了一点点。”杨老师接过我递给她的纸包,小心翼翼打开,当看到里面的白糖时,一把把我搂进怀里,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看着狭窄宿舍里围在她身边的我们一大群同学,杨秀珍老师俊美的脸上流下了两行热泪,也不知是因为腿伤疼痛的泪,还是为我们懂事而感动的泪。虽然脸上挂着泪珠,但明显可以看到她脸上的笑容。杨老师告诉我们,她最少有一个星期不能到学校给我们上课,叮嘱我们要认真学习,要遵守纪律,要听其他老师的话……
小时候的我虽然内心非常喜欢杨老师,但也很羞涩,不好意思表露得太明显,不像现在的孩子大胆。听到说她最少一个星期不能给我们上课,我的心里很失落,但更多的还是担心她的腿伤,想到她的腿都折了,肯定很痛苦,很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上学去得更早些。上学的小路就在我家隔壁,本可以直接走小路去,可我却非要绕道走到中学再从小路去学校,因为心里想着的是杨老师住在那里,巴不得在去上学的时候能看到她。她的腿还痛吗?和昨天比是不是要好了点?放学后,回家的路线也变成了走小路经过中学再回家,而且走到中学时脚步变得非常慢,特别是路过杨老师宿舍门口时,感觉跟蜗牛差不多,几米长距离要走好几分钟。眼睛盯着门口,其实心里也有点矛盾,盼望看到杨老师,又怕被她看到。她没去学校那个星期,我每天都从中学走小路去上学,哪怕下雨也要从那里走。
第三天,我的铅笔和作业本真的用完了,放学回到家又问妈妈要2角钱。妈妈便不高兴地问:“前天才给你的钱买笔和作业本,才过了两天,就又没有了?肯定撒谎了。你把钱用哪去了?”听到妈妈如此严厉,我才吞吞吐吐说了杨老师摔伤腿的事,用之前要的2角钱买了点白糖。妈妈听了,语气一下子温柔下来,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傻孩子,2角钱能买多少白糖?杨老师摔伤了腿,你还知道给老师买点东西去看看,说明我家裙子很懂事,懂得感恩老师,是个好孩子!你没钱买直接给我说啊!干吗要撒谎骗人?下次再不许这样!”说完就转身走了。等她再回到家时,手里除了我需要的铅笔和作业本外,还多了一包白糖,一包1斤装的白糖。妈妈又从屋后菜园里拔了几棵白菜和萝卜,连同那包白糖,用篮子装着,让我给杨老师送去。听妈妈这么说,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终于可以有理由看看杨老师她了。
我提着篮子,半跑半走很快就来到了中学。
还没到杨老师的宿舍,就看到她的宿舍门开着。来到门口,先伸头朝里面看,只见杨老师坐在一把高椅子上,旁边放着一张教室里用的没有靠背的长凳,凳子上坐着一个20多岁我不认识的年轻男子,也戴着一副眼镜,长得很帅。那个年轻男子正在给杨老师换药,杨老师发现了我。
“裙子,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心里盼望着很想见到杨老师又有些拘束的我,看到还有个陌生人在那里,就显得更加拘束。
“杨……杨老师,妈妈让我给你拿些白菜萝卜来……”平时说话挺利索的我,此时倒有点结巴起来。她看到我手里提着的篮子,正要说什么,我却把篮子放在宿舍地上,转身就跑了。
一个星期后,杨老师拄着拐杖来到学校上课。和她一起来的,还有那个在她宿舍里看到的那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杨老师向别人介绍,说那个年轻男子是她的未婚夫,也是一位下乡知青,在另一个乡镇当医生,腿摔伤后都是她未婚夫给她治疗和照顾她。本来杨老师腿伤都还没痊愈,还需要休息,可她认为自己一个星期都没给我们上课,已经耽误到了我们的学习,就坚持着要来学校给我们上课。她的未婚夫说服不了她,只能给她找来拐杖,同时还是放不下心,只好陪同着一起来学校。看到杨老师拄着拐杖也要来上课,我们都很感动,学习也比以前更上心努力。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好语文,要是学不好就对不起杨老师。
也许是杨老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改变了我吧,后来的我一直都很喜欢语文。多年以后,我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缺水那些事
小时候,我的家乡——正大,曾经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有女莫嫁正大营,干死蛤蟆饿死人;哪里有个牛脚凼,只见瓢瓜亮澄澄。”可见那个年代我家乡的冬季是多么的缺水。
我出生时正大当年还只是一个乡,2015以后由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大发展,才升级为镇。镇政府驻地正光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年居住着四五百户人家两千多人口,方圆十几里都算得上是大村寨。据村里老人说,正光村原先是一座古城,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了正大营城。“城”按方位建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除百姓外驻有守城官兵,当年也可堪繁华地,吸引来了许多湖南、江西籍等外来户。由于城内面积有限,后来的迁移户只能把家安在正大营“城”外,也就是现在的正大街。我家曾祖辈从江西挑盐做生意来到正大营城时,也把家迁来。
据说城内之前有一口非常大的水井,能供应居住在城内所有人口饮用及生活用水。驻守正大营城最大的官员姓熊,据说他家有一位千金小姐,有一次来水井边玩耍,回到家就重病卧床不起。那位大官急忙请来会巫术的仙娘,说原因就是小姐的魂魄掉井里了,必须用井填埋小姐才会有好转。水井填平就没了水,便有人说是熊家得罪水井菩萨,带着水源迁移去了别处。城外倒还有一口井,只是离正大街有三里地远,之前主要供应居住在街上的人家用水,被称为“凉水井”。
“凉水井”名不虚传,冬暖夏凉,特别是夏天,水冰冰凉凉的,人根本就不敢把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没了城内的井,它就成了主要水源地。春夏秋三季水量丰富,倒也能供应得上人们的日常用水,可到了枯水的冬季,加上村子其他小水井水量变少甚至干涸,到凉水井来挑水的人家就很多。凉水井从地下涌出水来的速度和水量,赶不上人们挑水的速度,先是水位下降,最严重时,里面的水只得用瓢一瓢一瓢往桶里舀。这时来挑水,就需在井边排队。
整个冬天,挑水守水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守水很费时间,白天妈妈根本没空,可一家人用水也是大事,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有时妈妈会让我挑着空水桶去井边,等轮到我舀满桶带口信回家,她才去把水挑回。而她就只能用三更半夜打着手电筒去守水,说那个时间别人都睡了,少有人还去挑水,她挑一桶回来就不需等太久。可妈妈毕竟是女人,黑灯瞎火走去水井边也害怕。可爸爸在离家几十里的村子教书,没法时妈妈就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带上打着哈欠的我去给她做伴:妈妈挑着水桶在前面走,我拿着手电筒跟在她身后。来到井边如果运气好不用等也能舀满一担,也有时去得不是时候,在去的路上碰到才正挑水回家的人,这样我们就得在水井边守上一段时间。守水的过程中,我的瞌睡又来了,哈欠一个接着一个,妈妈怕我睡着,总会说一些让人感兴趣的话,让我提起精神来。
不知何时开始,村子里头脑灵活的人家买了马车,赶着马车在附近几个乡镇赶“转转场”做起了生意:从这个集市上买来米糠、黄豆之类,运到那个集市上去卖,顺便在那个集市再买一些白菜芹菜等运到下一个集市,从中赚一些差价,挣的钱比干农活要多得多。我家堂哥就是最早买马车做生意的人,他把这样的好处和我爸妈说了,爸妈一合计也买了一辆。爸爸要教书不能做生意,妈妈就从田地里解放出来,也像堂哥那样赶着马车东奔西走。妈妈本来就很勤劳能干,她在附近几个乡镇赶集,发现别的乡镇不缺水,而且有些地方水源就在马路边上——于是从此赶着马车去赶集时,马车上不是多了一袋需要洗的脏衣物,就是多了几个带盖的盛水桶,妈妈会利用赶集回来的路上在有水的路边把衣物洗了,或者把桶装满水,用马车拉回家。
自从买了马车,我和妈妈就再也不用三更半夜去水井守水了。
土墙边的快乐
爷爷留下的三间木屋在分家时被平分成两家,一家一间半,叔叔家住左边,我家住右边。叔叔家与东凤家相邻,两家房子间隔两米,中间有一条水沟,水沟延伸到叔叔家菜园里那棵野柿子树下左拐,又从我家的菜园中间穿过。从我记事起,这条水沟就有了。听村里大人说,水沟源头在龙塘河水库,穿过整个正大营城,绕到正大街上,因为从我家菜园穿过能灌溉到更多农田,所以那条水沟就选择从我家菜园中间穿过。
水沟主要用于每年春夏两个季节灌溉水稻,从龙塘河水库开闸放过来的水,通过水沟一直输送到正大,用来保障我们几百亩农田的农用水。
龙塘河水库位于湘黔交界的凤凰县落潮井镇境内,与松桃正大接壤。从空中俯瞰龙塘河,就是一条活生生的巨龙。水库总库容285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6万余亩,是一座以灌溉、防洪为主,兼以人饮、发电、环保为辅的中型水利工程。修建于1974年冬,一个人定胜天的年代,施工现场是千军万马,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一石一柱全靠人力垒砌,短短九个月就基本建成,创造了凤凰、松桃正大人民引以为豪的“龙塘河”精神。
经过我家菜园的这条水沟,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水。每年秋冬两季,水沟干涸,住在附近的人家有时为了自己方便,会偷偷往里面扔一些垃圾,沟坎边没有人家的地方会疯长一些杂草野刺,慢慢塞满沟道。每年开春,村长都会组织村民进行沟渠清理维护,大家用铲子把扔在里面的垃圾和一些淤积的泥土一铲铲铲出,用刀砍掉沟渠边的杂刺野草,不致影响开春后沟渠过水。
叔叔家柿子树旁还有棵银杏树,不知什么时候栽的,从记事起它就长在那里,好像长不大,四五岁有记忆开始在树下玩时是多大,四五年过去了感觉还是那么大。别的树每年都会开花有的也会结果,这棵银杏树似乎就从未开过花结过果。倒是东凤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过“母银杏树才能开花结果,这棵银杏树是公的,不能开花结果”。她说出来的时候,我、珍爱、珍珍还嘲笑过她:“树也有公的母的?不懂不要乱说!”我们喜欢银杏树叶子的形状,觉得像一把把扇子,还像一只只蝴蝶。
银杏树靠着一堵土夯墙。是珍爱家的,一尺多厚,墙内是她家的茅房。我们小孩子都喜欢银杏树的叶子,没事时就喜欢爬上土墙去摘,也不在乎茅房的气味。翻爬一多,都被爬得光溜溜了。
正大没有河,只有一座水库,每年夏天,总会有人要去洗澡。说来也很邪乎,差不多每年都有人被淹死,有大人也有小孩。每到这时,我妈每天都不许我到水边去玩耍,哪怕很浅的水沟也不行。
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照耀着大地,哪个小孩子能抵挡得住玩水的诱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并责骂我们玩水,从我家菜园中间穿过的那条水沟成了我们的秘密通道。太阳天,我、东凤、珍爱、珍珍会悄悄来到菜园,找个隐蔽位置,从别处搬来石头堆在沟里,用泥巴堵塞好石缝,让水位变高。水沟有人管理,有时候管理员发现下游的水量减少或者不再流动,不用想也知道是我们这些调皮孩子把水拦断了好玩水。就沿着水沟检查,发现了被拦断的地方,就要我们立刻清理,要么他直接动手把石头掀开扔掉。可他也不可能一整天守着我们,一离开,我们又重新捡回石头,再把水堵住。
等水没过小腿肚,我们穿着衣裤开始在沟里游泳或者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说游泳,不过是用肚皮贴在沟里一阵乱爬,衣裤湿漉漉沾满泥巴,看不到原来的颜色。满身的泥巴是不敢直接回家的,怕大人们会发现,我们常常还会从家里偷拿一点洗衣粉,把自己弄脏的衣服脱下来揉搓,在水沟里清洗干净,拧干水又穿在身上。衣服还是湿的,得等干了才能回去。大家就这样穿着湿衣服爬上土墙,要么抓着树枝悬在银杏树上晒,要么撅着屁股晒,悬累了,撅累了,干脆坐上土墙对着太阳晒。夏天气温高,个把小时过去,我们一个个的小脸被太阳晒得黢黑发亮,穿在身上的湿衣服一干,大家开心得不得了,想着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大大方方的回家,大人们也就不会发现我们今天在玩水,并为我们自以为是的聪明而自豪。可我们坐在土墙上,屁股的位置还有泥巴的痕迹。出来大半天,脸也晒得黢黑,大人们能不发现我们的秘密吗?其实他们早已经发现,只不过没说破,我们还天真的认为自己做得很隐秘,相约明天还去继续我们的快乐。
“柴刀木匠”叶二伯
珍爱她爹,在正大那条街上,与我平辈的大小孩子大多称呼他为“叶二伯”。珍爱家妈妈是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照辈分我得称呼“叶二伯”为姑爷。他左脚有点跛,听说是年轻时干活摔伤落下的残疾。我们不在意他的残疾究竟是天生还是后来什么变故造成的,没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行。
叶二伯家子女很多,三男三女,珍爱,珍珍两个女儿排行第四和第五。珍爱大我两岁半,珍珍和我同岁。小时候没什么电视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无事时都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一块儿玩耍或者做游戏。除了东凤之外,珍爱珍珍两姐妹是与我一块儿玩得最多的小伙伴。
叔叔家那棵银杏树靠着的一堵土墙上,是珍爱家的,土墙内是她家的茅房。小时候家家户户的茅房都在房子外面,挖一个大大的正方形土坑,四周包括底部用锤子砸严实,防止漏粪水。坑修好了,先在上面用直径15厘米左右木头按两尺左右的距离平铺一排,再在木头上铺一些2厘米左右厚的木板,木板间还得预留下等距隙缝,方便以后养猪时猪拉的粪便漏下土坑去。还要找四根直径30厘米左右1米多高的柱子,立在铺好木板的土坑四周围加上横梁围成栏,里面用来养猪。为了如厕方便,每家又会选择正方形的一边留出两尺左右宽的地方做蹲位。人和猪拉的粪都装在坑里,发酵后用来当肥料浇庄稼。
珍爱家茅房的那一堵土夯墙,有一尺多厚,很结实,立在那里有好几年了。每年春夏秋三季,我们喜欢去银杏树那里看或者捡摘银杏叶,那堵土墙早被我们爬得光溜溜的了。
茅房顶扎盖着茅草,珍爱曾对我们说过:“你们知道喂猪上厕所的地方为什么叫茅房吗?就因为是用茅草做的房子,就像我家这种;你们家的房顶盖的瓦,就叫茅厕。除了我家有茅房其他家都没有。”她的脸上很是得意。我们也同意她的话,确实在家里爸爸妈妈都把那地方叫茅厮。珍爱家茅房三面围着玉米秆,算是用来遮羞的墙;前面是一个框,挂一块黑色油毡布像门帘。
珍爱她爹叶二伯有一个诨名叫“柴刀木匠”——我们那里的意思是调侃那些本不是木匠却喜欢跨行做木匠活却马虎又做不好的人。
叶二伯当然不是木匠,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听说他干活动作利索,就是不太讲究质量;他家茅房就是他领着一家大小搭建的,一年要修补两回。除了那堵土墙像定海神针般非常牢固之外,其他的都松松垮垮。
茅房禁不起风吹雨打,不要说狂风暴雨,就是风雨稍微大点也可能倒塌。每次大风雨过后,她们家最关心的就是茅房倒塌了没有。如果没有倒塌,全家都会庆幸;倒塌了,叶二伯会等到天放晴后,带领一家大小再重新搭建。
搭建茅房的材料不用精心挑选,眼睛看到什么合适就用什么,比如支撑的架子像拳头大小的烧火柴,只要高度够就行,房顶就用刚砍下来的玉米秆……这些材料哪里经得起风吹日晒。
“叶二伯,修茅房,半天能搭一座房。随便找来几根棒,柴刀斧头一起上。草做房顶柴做墙,十天半月下场雨,又垮房顶又倒墙。半年又要修一次,叮叮当当全家忙。”这是对门表婆随口编的顺口溜,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叶二伯家修茅房的独特技艺以及他们家频繁修房的无奈。
反复修缮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叶二伯不得不每隔半年就进行一次大修。全家人忙得不可开交,叮叮当当的声音此起彼伏,让人听着都心疼。
茶山·马车·妹妹
“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晚上7点钟,在昌文家院坝集中开会,有重要事情通知。”村长叶老满拿着个高音喇叭从街上走过,边走边喊。
在离家几十里一个村子里教书的爸爸,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家里的大小事情几乎都是妈妈在做,今晚的会也只能是妈妈去参加。开完会回来,因为爸爸不在家,开会的内容就只能告诉我们几姊妹:“望龙坡和蒙子树这些山坡要改种茶了。”
“妈,那些山上不是有好多枞树和油茶树吗?怎么种茶?”
“村长说这几年山上的枞树和油茶树被砍了很多,山林都快没了,要挖掉,听说还是用什么挖土机来挖,挖了种茶……”
妈妈说这些其实我们都不太听得懂,听懂了也没用。妈妈可能因为爸爸不在家,只想把今晚的会议内容告诉家人,所以就说给我们听了。
望龙坡和蒙子树这些山坡,原本满山遍野生长着高大的枞树、油茶树以及别的一些灌木,密密麻麻的。我们小孩子一两个人是不敢轻易进入山林,因为山林太茂密,容易迷山。大家去放牛砍柴也总是三五个一起,在山林里还故意大声说话,时不时还要互相吆喝几声,目的就是想让小伙伴们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也给自己壮壮胆。
村子里家家户户做饭、取暖都是烧木柴。谁家没烧的了,拿着柴刀、斧头上山,遇到枞树砍枞树,遇到油茶树就砍油茶树。大人砍大树,小孩捡树枝丫,挑回家成了每家每户的柴火。没几年,山上大量的树木消失了,政府部门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想方设法设立一些乡规民约来制止。可一些村民法律意识、环境意识都很淡薄,认为又不是自己一家人砍的,而且砍一两棵也不会影响很大,不至于把树都砍没了。正因为大家都抱着这种自私的想法,还生怕砍少了自己家吃亏,结果越发不可收拾,都像疯了一样,短短几年,山坡上就再也看不到高大的树木。本来就缺水的地方,雨水就更珍贵;由于森林被破坏,有些地方还造成了水土流失,下雨时间稍长,雨水无法储存,不是这里滑坡,就是那里田坎被冲毁。而长时间不下雨,田地里又因缺水而干旱,庄稼欠收或无收……
乡政府换了新领导,据说新乡长上任后立刻行考察调研,走访了解到正大土地肥沃,那些被砍掉树木后的荒芜山坡,长满杂草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便请来专家评估论证,结论是这里无论是土质、气候还是海拔高度都非常适合种茶树,不仅能保持水土不流失,产出的茶叶还能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争取到的正大万亩茶场的建设开工了,需要把那些被砍掉树木只留下杂草的荒坡开垦出来,政府从外地请来挖掘机和推土机,刨出了那些被砍掉树干而留在地里的树桩和树根和泥土。那段时间,村民们每天跟在推土机旁,哄抢被推出来的树桩,运回家当柴烧似乎成了很重要的事。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去上学时,就看到大人们在推土机旁哄抢。到了周末或下午3点后我们放学,大人们就把继续抢树桩的任务交给孩子,围在推土机旁的人就全换成了小孩。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13岁,正上初中,弟弟10岁,妹妹6岁。抢推土机推出来的树桩,村子里男孩子最厉害,都和我差不多大,不仅力气大,胆子也大,有时推土机刚推出一截树桩,就有人立刻冲到推土机前,死死抱着不放手,也不怕被推土机伤到。因为这种抢法,开推土机的叔叔一直吼吼骂骂。可无济于事,那些“勇敢的”、无所畏惧的小孩根本听不进去,大树桩总是在刚露出一截就被抢了。我一个女孩子胆子小,争抢不过他们,只能默默地跟在推土机后面,捡一些别人看不上的小枝小条。有时候运气好也能捡到一两棵被泥土盖住,别人没发现的大一点的树桩。
家里有一辆马车,妈妈用来在周围几个乡镇赶集做生意。都是天一亮就出发,赶完集回到家天基本黑了,很辛苦。妈妈说赶集要早点,才能从农户手里买到第一手货,价格要便宜点,转手卖才有钱赚。去晚了,集市上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要么买不到,要么买别人转手高价卖的,这样再转手卖就只能赚很少的钱。有时候她也会根据某个集市上生意情况选择休息一天。
既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又很懂事,妈妈去赶集了,我放学后或是周末就会帮着做一些事情。
赶着马车带上妹妹去山上捡柴的那天是星期六,妈妈说她有点不舒服,不去赶集休息一天。我于是要妈妈允许我赶着我家马车去。
“你会赶马车吗?要先给马套上鞍子,最后要把车卸下,让马吃草的,这些你会吗?”
“会,你给马套马鞍拉车我都偷偷看着,早学会了。”我骄傲地回答。
“呵,是真的吗?”妈妈有点惊讶。
“那你先给马套上马鞍拉上车,我看看做得像不像,能做你就赶去。”
听妈妈答应了,便想在她面前表露一番。很快找来马拉车的全部工具,学着妈妈给马套鞍的样子,动作利索几下子就把马车套在了马背上。妈妈看我真的会套马车,笑着同意了,只是反复叮嘱要注意安全。
把要带的工具放在马车上,准备出发时,6岁的妹妹突然从屋里跑出来,爬上马车,嚷着要和我一块去。妈妈本不想让她去的,可妹妹紧紧抓住马车不肯下车。妈妈只能同意,要我绝对照顾好妹妹。担心妹妹中途睡着,妈妈又从家里扔来一个麻袋,说垫在屁股下坐;如果妹妹在山上想睡觉了,铺开,让她睡在上面。在妈妈的絮絮叨叨下,我带着妹妹,驾着马车往山上走去。
来到山坡上,发现推土机没工作。空荡荡的山上,除了新翻的大片大片泥土,也能发现一些别人看不上的小枝细条的柴火。我还觉得今天没了别人争捡,捡起柴来更得心应手,不一会就捡了一小堆。抬头看看天,有点变了,刚才都还好好的,这会变得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了。但我得捡一马车拉回去,这点柴太少了。妹妹刚来到山上时,也帮着捡了一些,可才没多久,就不想做了。我把麻袋放在那堆捡来的柴边,让她坐在上面。我还要去别的地方继续捡,告诉她别离开,看着那堆柴,等我回来。妹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我朝另一个地方继续捡。哇!运气太好了,可能是之前推土机工作的时候没有抢柴的人,泥土里竟然堆着好多大树桩。我抑制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很认真捡着那些柴,连天空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也没感觉到。
“呜呜!大姐——你在哪里?我害怕!”猛然间听到妹妹的哭喊声。我把妹妹忘记了。
终于在田野另一端找到妹妹时,她已经离开了先前待着的地方,手中紧握着她垫坐的那只麻袋。在这个细雨绵绵的午后,新翻的泥土在雨水的洗礼下变得湿滑而粘稠,妹妹手中的麻袋已被泥土染得一片狼藉,那些湿泥不仅覆盖了麻袋原本的质地,还粘附得她满手、满身,甚至满脸。
她那因哭泣而沾满泥浆的小脸蛋,雨水泪水交混,使得她看上去几乎无法辨认。此刻的她,活脱脱就像一个刚从泥潭中滚出来的泥人偶,既让人心疼又让人忍俊不禁。尽管如此,看着她这副模样,我的心中更多的是自责和懊悔。妈妈明明再三叮嘱我要照顾好妹妹,而我却……
就在我怔怔出神之际,妹妹那双明亮的眼睛发现了我的存在。她立刻大声哭喊起来,声音中充满了委屈和迫切,嚷嚷着要立刻回家。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心如同被针扎一般疼痛,顾不得其他,更没心思去考虑那些捡拾的柴火是否要运回家的问题。我迅速驾上马车带上妹妹,驱赶着马车向家里奔去。
编后:我们确实很少舍得把一个一万多字的版都给一个几乎是“初出茅庐”的作者的。而且,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还不难发现,组成“记忆”的这五题文字,一定只有作者才能知道被“编辑”在所难免删掉了多少字句的同时,更还被缩小了半个字号。
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阅读了这些温婉清和的文字,就不会对作者温婉清和地织就描摹的这一厢温婉清和的情感无动于衷。而我们也正是历来就反感和反对
矫揉造作故作声势惺惺作态,尤其腻味将心绪情怀凌空蹈虚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何况,似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有多少人不是总在感叹、感慨着生活、生命的匆匆忙忙惶惶恐恐慌慌张张呢?那么,如果你终于从这些文字里获得了一丝儿的温暖一会儿的安静,我们都是有理由备受鼓舞的。
春节前夕我们得知,松桃大兴有这么一个由最初的5人于2023年10月创建的纯民间文学组织“大兴文学沙龙”,不过一年多点时间,会员就发展到18人,创作作品170余篇逾25万字。半信半疑可有可无溜进他们的网上园地一瞟,还是按捺不住“心动”起来。只是因于《梵净山周末》不止于“文苑”栏的稿源,众所周知地从来就丰沛得令人爱不释手;而我们的“行动”,由于随手选出其中5人的作品来打算刊载的文字数量竟有足足两个版面还余,于是只好选择“连载”方式的第一期刊载的《小白》和《安置区》两题,也就情有可原地被延宕到了3月21日。但加上于28日“连载”的《故土》和本期的《大兴记忆》,我们对这个草根组织的关注热情和程度,亦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也不说作为全国的首个扎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文学组织,为移民安置区所开辟的文化建设新路径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仅是当初那5位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在社会最基层的社区点亮的文学之灯,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可以不嫌絮叨啰嗦地引用一下崔颢的两句诗来略证我们的心怀——此情此景,不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另一种写照吗?
而且显然,盈车嘉穗穰穰满家也一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