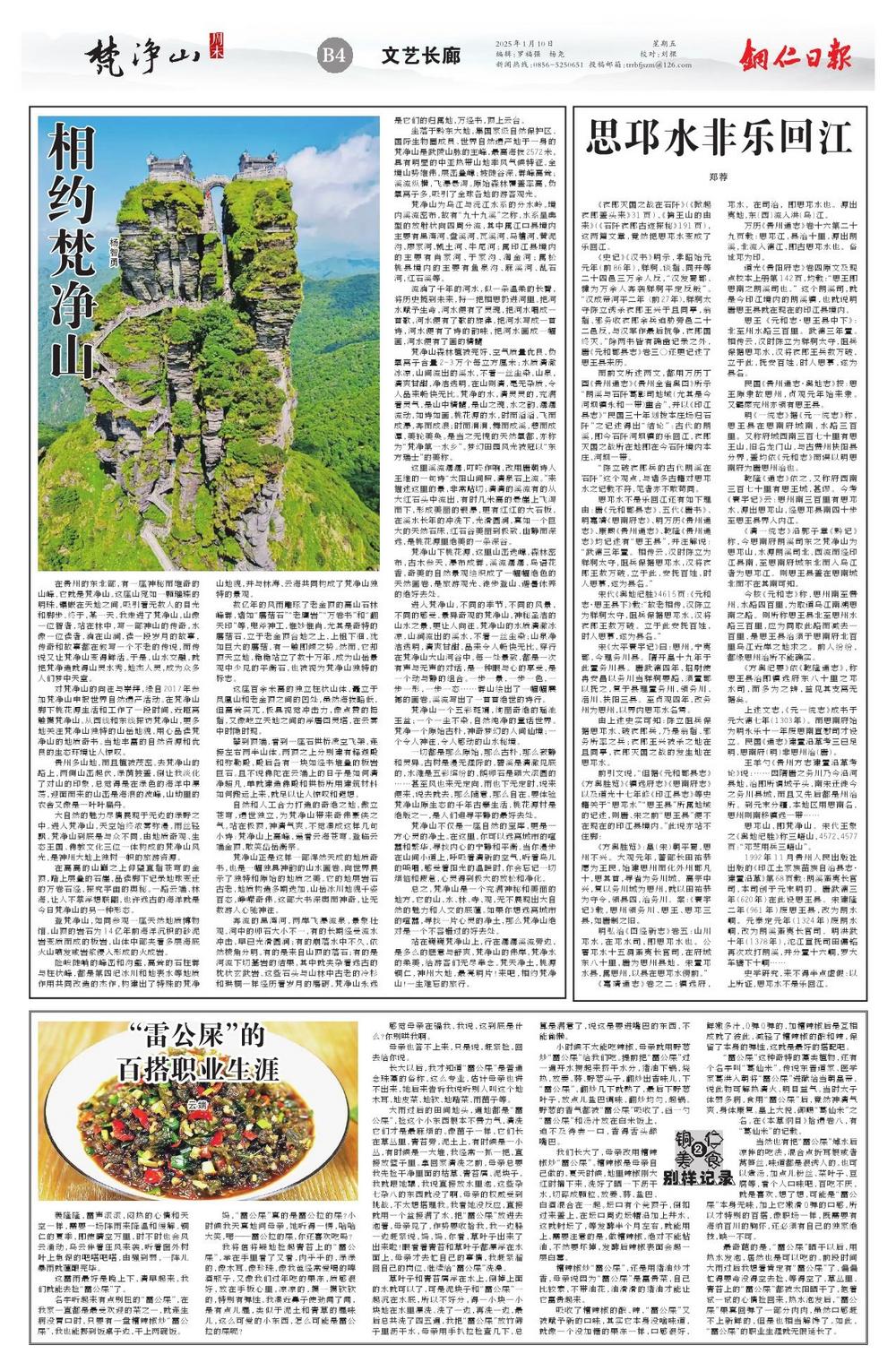轰隆隆,雷声滚滚,闷热的心情和天空一样,需要一场阵雨来降温和缓解。铜仁的夏季,即使晴空万里,时不时也会风云涌动,乌云伴着狂风来袭,听着窗外树叶上急促的吧嗒吧嗒,由强到弱,一阵儿暴雨就蕴酿完毕。
这雷雨最好是晚上下,清早起来,我们就能去捡“雷公屎”了。
名字听起来有点别扭的“雷公屎”,在我家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菜之一,就连生病没胃口时,只要有一盘糟辣椒炒“雷公屎”,我也能挪到饭桌子边,干上两碗饭。
妈,“雷公屎”真的是雷公拉的屎?小时候我天真地问母亲,她听得一愣,哈哈大笑,嗯——雷公拉的屎,你还喜欢吃吗?
我将信将疑地捡起青苔上的“雷公屎”,举在手里看了又看,肉乎乎的,绿绿的,像木耳,像珍珠,像我爸经常爱喝的啤酒瓶子,又像我们过年吃的果冻,质感很好,放在手板心里,凉凉的,摸一摸软软的,特别有弹性。我凑近鼻子使劲闻了闻,是有点儿腥,类似于泥土和青草的腥味儿,这么可爱的小东西,怎么可能是雷公拉的屎呢?
感觉母亲在骗我,我说,这到底是什么?你别哄我啊。
母亲也答不上来,只是说,赶紧捡,回去给你说。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雷公屎”是普通念珠藻的俗称,这么专业,估计母亲也讲不出来,她后来告诉我说听别人叫这个地木耳、地皮菜、地软、地踏菜、雨菌子等。
大雨过后的田间地头,遍地都是“雷公屎”,捡这个小东西根本不费力气,清洗它们才是最麻烦的。像菌子一样,它们长在草丛里,青苔旁,泥土上,有时候是一小丛,有时候是一大堆,我经常一抓一把,直接放篮子里。拿回家清洗之前,母亲总要我先捡干净里面的枯草、青苔屑、泥块子。我就跟她犟,我说直接放水里泡,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没了啊。母亲的权威受到挑战,不太想搭理我。我看她没反应,直接就用一个盆接满了水,把“雷公屎”放进去泡着,母亲见了,作势要收拾我,我一边躲一边赶紧说,妈,妈,你看,草叶子出来了出来啦!眼看着青苔和草叶子都漂浮在水面上,母亲才去忙自己的事情,我赶紧溜回自己的岗位,继续给“雷公屎”洗澡。
草叶子和青苔屑浮在水上,倒掉上面的水就可以了,可是泥块子和“雷公屎”一起沉在水底,所以不好分,得一小块一小块地在水里漂洗。洗了一边,再洗一边,最后总共洗了四五遍,我把“雷公屎”放竹筛子里沥干水,母亲用手扒拉检查几下,总算是满意了,说这是要进嘴巴的东西,不能偷懒。
小时候不太能吃辣椒,母亲就用野葱炒“雷公屎”给我们吃。提前把“雷公屎”过一遍开水捞起来挤干水分,猪油下锅,烧热,放姜、蒜、野葱头子,翻炒出香味儿,下“雷公屎”,翻炒几下就熟了,最后下野葱叶子,放点儿盐巴调味,翻炒均匀,起锅。野葱的香气都被“雷公屎”吸收了,舀一勺“雷公屎”和汤汁放在白米饭上,迫不及待尝一口,香得舌头舔嘴巴。
我们长大了,母亲改用糟辣椒炒“雷公屎”。糟辣椒是母亲自己做的。夏天时候,地里辣椒刚大红时摘下来,洗好了晒一下沥干水,切碎成颗粒,放姜、蒜、盐巴、白酒混合在一起。坛口有个瓮顶子,倒扣过来盖上,在坛口周边坛帽沿加上井水,这就封坛了,等发酵半个月左右,就能用上。需要注意的是,做糟辣椒,绝对不能粘油,不然要坏掉,发酵后辣椒表面会起一层白霉。
糟辣椒炒“雷公屎”,还是用猪油炒才香,母亲说因为“雷公屎”是富贵菜,自己比较素,不带油花,油滑滑的猪油才能让它富贵起来。
吸收了糟辣椒的酸、辣,“雷公屎”又被赋予新的口味,其实它本身没啥味道,就像一个没加糖的果冻一样,口感很好,鲜嫩多汁,Q弹Q弹的,加糟辣椒后是互相成就了彼此,减轻了糟辣椒的酸和辣,保留了本身的弹性,这就是最好的搭配吧。
“雷公屎”这种奇特的藻类植物,还有个名字叫“葛仙米”。传说东晋道家、医学家葛洪入朝将“雷公屎”进献给当朝皇帝,说此物可解热清火、明目益气。当时太子体弱多病,食用“雷公屎”后,竟然神清气爽,身体康复。皇上大悦,御赐“葛仙米”之名。在《本草纲目》拾遗卷八,有“葛仙米”的记载。
当然也有把“雷公屎”焯水后凉拌的吃法,混合点折耳根或者莴笋丝,味道都是很诱人的。也可以煮汤,加点儿粉丝、菜叶子、豆腐等,看个人口味吧,百吃不厌,就是喜欢。想了想,可能是“雷公屎”本身无味,加上它嫩滑Q弹的口感,所以才特别的百搭,像职场一样,既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还必须有自己的独家绝技,缺一不可。
最奇葩的是,“雷公屎”晒干以后,用热水发泡,居然也是可以吃的。前段时间大雨过后我想着肯定有“雷公屎”了,偏偏忙得要命没得空去捡,等得空了,草丛里、青苔上的“雷公屎”都被太阳晒干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捡回来,热水泡发后,“雷公屎”果真回弹了一部分肉肉,虽然口感赶不上新鲜的,但是也相当解馋了。如此,“雷公屎”的职业生涯就无限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