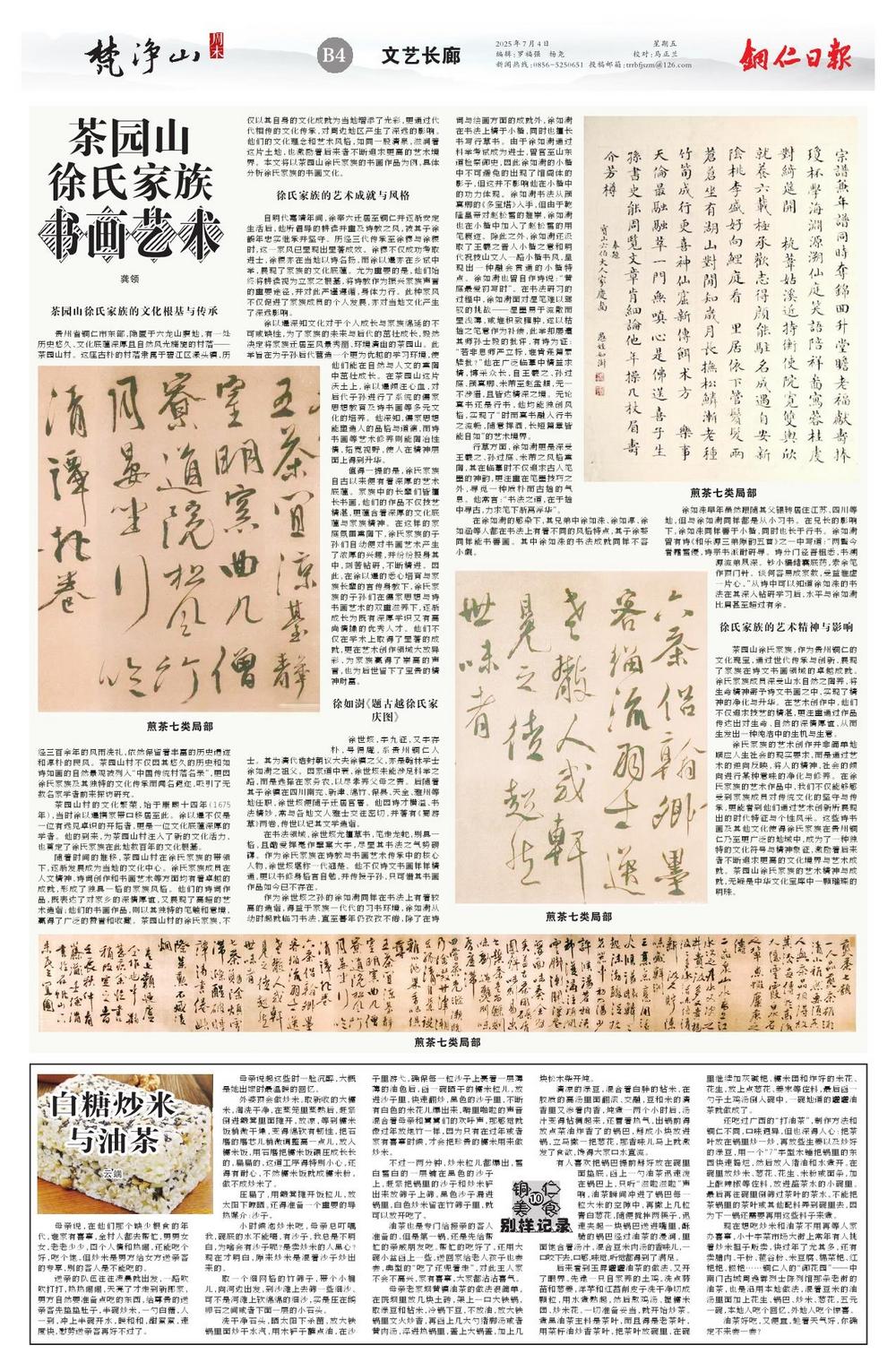母亲说,在他们那个缺少粮食的年代,谁家有喜事,全村人都去帮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图个人情和热闹,还能吃个好,吃个饱。但炒米是男方给女方送亲客的专享,别的客人是不能吃的。
送亲的队伍往往凌晨就出发,一路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天亮了才走到新郎家,男方自然要准备点吃的东西,给尊贵的送亲客先垫垫肚子,半碗炒米,一勺白糖,人一到,冲上半碗开水,暖和和,甜蜜蜜,速度快,慰劳送亲客再好不过了。
母亲说起这些时一脸沉醉,大概是她出嫁时最温暖的回忆。
外婆顶会做炒米。取新收的大糯米,淘洗干净,在蒸笼里蒸熟后,赶紧倒进簸箕里面摊开,放凉,等到糯米饭稍微干燥,变得绵软有韧性,把石磨的磨芯儿稍微调整高一点儿,放入糯米饭,用石磨把糯米饭碾压成长长的,扁扁的,这道工序得特别小心,还得有耐心,不然糯米饭就成糯米粉,做不成炒米了。
压扁了,用簸箕摊开饭粒儿,放太阳下晾晒。还得准备一个重要的导热媒介:沙子。
小时候泡炒米吃,母亲总叮嘱我,碗底的水不能喝,有沙子,我总是不明白,为啥会有沙子呢?是卖炒米的人黑心?现在才明白,原来炒米是混着沙子炒出来的。
取一个细网格的竹筛子,带个小桶儿,向河边出发,到沙滩上去筛一些细沙。可不是河滩上软绵绵的细沙,实是压在鹅卵石之间或者下面一层的小石头。
洗干净石头,晒太阳下杀菌,放大铁锅里面炒干水汽,用木铲子蘸点油,在沙子里游弋,确保每一粒沙子上裹着一层薄薄的油色后,舀一碗晒干的糯米粒儿,放进沙子里,快速翻炒,黑色的沙子里,不断有白色的米花儿爆出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混合着母亲和舅舅们的欢呼声,那感觉就像过年放炮竹一样,因为只有在过年或者家有喜事时候,才会把珍贵的糯米用来做炒米。
不过一两分钟,炒米粒儿都爆出,雪白雪白的一层铺在黑色的沙子上,赶紧把锅里的沙子和炒米铲出来放筛子上筛。黑色沙子漏进锅里,白色炒米留在竹筛子里,就可以放开吃了。
油茶也是专门给接亲的客人准备的。但是第一锅,还是先给帮忙的亲戚朋友吃。帮忙的吃好了,还用大碗小盆舀上一些,送回家给老人孩子也尝尝,典型的“吃了还兜着走”,对此主人家不会不高兴,家有喜事,大家都沾沾喜气。
母亲老家坝黄镇油茶的做法很简单,在院坝里放几块土砖,架上一口大铁锅,取绿豆和粘米,冷锅下豆,不放油,放大铁锅里文火炒香,再舀上几大勺猪脚汤或者黄肉汤,淬进热锅里,盖上大锅盖,加上几块松木柴开炖。
清凉的绿豆,混合着白胖的粘米,在胶质的高汤里面翻滚、交融,豆和米的清香里又渗着肉香,炖煮一两个小时后,汤汁变得粘稠起来,还冒着热气,出锅前得放点菜油炸香了的锅巴,掰成小块放进锅,立马撒一把葱花,那香味儿马上就激发了食欲,馋得大家口水直流。
有人喜欢把锅巴提前掰好放在碗里面垫底,舀上一勺油茶迅速泼在锅巴上,只听“滋啦滋啦”声响,油茶瞬间冲进了锅巴每一粒大米的空隙中,再撒上几粒青白葱花,随便搅拌两筷子,迅速夹起一块锅巴送进嘴里,酥脆的锅巴经过油茶的浸润,里面饱含着汤汁,混合豆米肉汤的香味儿,一口咬下去,口感,味觉,听觉都得到了满足。
后来看到玉屏罐罐油茶的做法,又开了眼界。先逮一只自家养的土鸡。洗点蒜苗和葱姜,洋芋和红苕削皮子洗干净切成颗粒,用水煮熟起,然后熬鸡汤、捏糯米团、炒米花。一切准备妥当,就开始炒茶。煮黑油茶主料是茶叶,而且得是老茶叶,用菜籽油炒香茶叶,把茶叶放碗里,在碗里继续加灰碱粑、糯米团和炸好的米花、花生,放上点葱花、姜末等佐料,最后舀一勺子土鸡汤倒入碗中,一碗地道的罐罐油茶就做成了。
还吃过广西的“打油茶”,制作方法和铜仁不同,口味迥异,但也深得人心:把茶叶放在锅里炒一炒,再放些生姜以及炒好的绿豆,用一个“7”字型木锤把锅里的东西快速捣烂,然后放入猪油和水煮开。在碗里放炒米、葱花、花生、米粉或面条,加上酸辣椒等佐料,放进盛茶水的小碗里。最后再往碗里倒筛过茶叶的茶水。不能把茶锅里的茶叶或其他配料弄到碗里去,因为下一锅还需要再用这些料子来煮。
现在想吃炒米和油茶不用再等人家办喜事,小十字菜市场大街上常年有人挑着炒米担子贩卖,快过年了尤其多,还有卖腊肉、干粉、苞谷粉、米豆腐、棉菜粑、红粑粑、糍粑……铜仁人的“御花园”——中南门古城周逸群烈士陈列馆那条老街的油茶,也是沿用本地做法,混着豆米的油汤里面加上花生、锅巴、炒米、葱花,五元一碗,本地人吃个回忆,外地人吃个惊喜。
油茶好吃,又便宜,趁着天气好,你确定不来尝一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