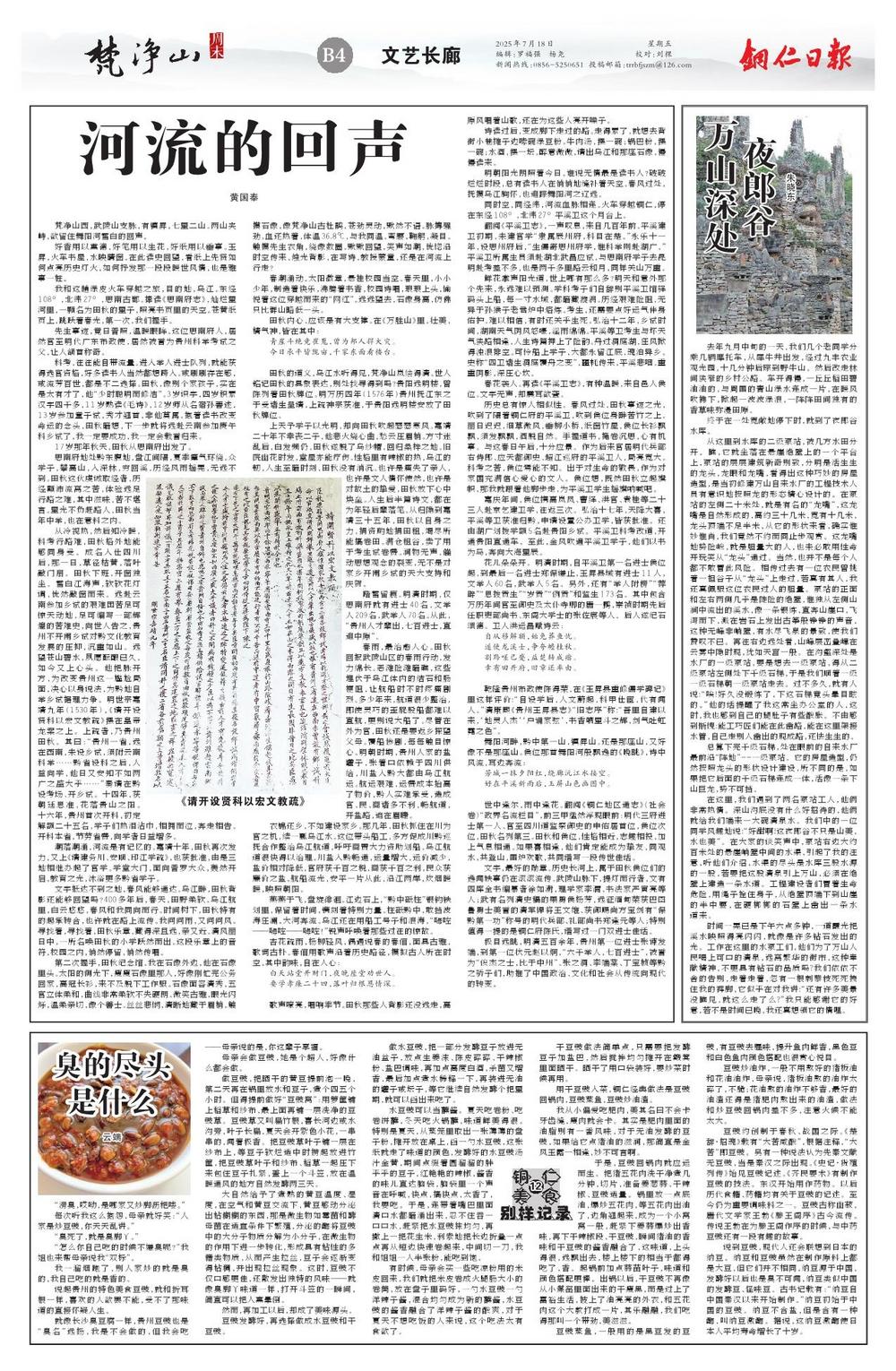“滂臭,哎呦,是哪家又炒脚沥粑喽。”
每次听我这么抱怨,母亲就好笑:“人家是炒豆豉,你天天乱讲。”
“臭死了,就是臭脚丫。”
“怎么你自己吃的时候不嫌臭呢?”我姐也来帮母亲说我“双标”。
我一溜烟跑了,别人家炒的就是臭的,我自己吃的就是香的。
说起贵州的特色美食豆豉,就和折耳根一样,喜欢的人欲罢不能,受不了那味道的直接怀疑人生。
就像长沙臭豆腐一样,贵州豆豉也是“臭名”远扬,我是不会做的,但我会吃——母亲说的是,你这辈子享福。
母亲会做豆豉,她是个超人,好像什么都会做。
做豆豉,把晒干的黄豆提前泡一晚,第二天再在锅里放水和豆子,煮个四五个小时。但得提前做好“豆豉窝”:用箩筐铺上稻草和纱布,最上面再铺一层洗净的豆豉草。豆豉草又叫扁竹根,喜长河边或水沟旁,叶子长扁,夏天会开紫色小花,一串串的,闻着极香。把豆豉草叶子铺一层在纱布上,等豆子软烂适中时捞起放进竹筐,把豆豉草叶子和纱布、稻草一起压下来包住豆子扎紧,盖上一个斗笠,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自然发酵两三天。
大自然给予了煮熟的黄豆温度、湿度,在空气和黄豆交流下,黄豆感动分泌出粘糊糊的东西,那是微生物如霉菌和酵母菌在适宜条件下繁殖,分泌的酶将豆豉中的大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进一步转化,形成具有粘性的多糖类物质,从而产生拉丝,豆子会逐渐变得粘稠,并出现拉丝现象。这时,豆豉不仅口感更佳,还散发出独特的风味——就像臭脚丫味道一样,打开斗笠的一瞬间,简直可以把人熏晕倒。
然而,再加工以后,却成了美味源头。
豆豉发酵好,再选择做成水豆豉和干豆豉。
做水豆豉,把一部分发酵豆子放进无油盆子,放点生姜沫、陈皮碎碎、干辣椒粉、盐巴调味,再加点高度白酒,杀菌又增香,最后加点煮水稀释一下,再装进无油的罐子或坛子,等它继续自然发酵个把星期,就可以舀出来吃了。
水豆豉可以当蘸酱。夏天吃卷粉、吃卷饼蘸,冬天吃火锅蘸,味道鲜美得很。特别是夏天,从蒸笼里取出一张薄薄的盘子粉,摊开放在桌上,舀一勺水豆豉,这张纸就走了味道的颜色,发酵好的水豆豉汤汁金黄,期间点缀着圆溜溜的胖乎乎的豆子,红艳艳的辣椒,酱香的味儿直达脑袋,脑袋里一个声音在呼喊,快点,搞快点,太香了,我要吃。于是,连带着嘴巴里面清口水都暗涌出来,忍不住吞一口口水,赶紧把水豆豉抹均匀,再撒上一把花生米,利索地把长边折叠一点点再从短边快速卷起来,中间切一刀,我和姐姐一人半张粉,能吃到饱。
有时候,母亲会买一些吃凉粉用的米皮回来,我们就把米皮卷成火腿肠大小的卷筒,放在盘子里码好,一勺水豆豉一勺洋辣子酱,混合均匀成为新的蘸酱,水豆豉的酱香融合了洋辣子酱的酸爽,对于夏天不想吃饭的人来说,这个吃法太有食欲了。
干豆豉做法简单点,只需要把发酵豆子加盐巴,然后搅拌均匀摊开在簸箕里面晒干。晒干了用口袋装好,要炒菜时候再用。
用干豆豉入菜,铜仁经典做法是豆豉回锅肉,豆豉蒸鱼,豆豉炒油渣。
我从小偏爱吃肥肉,美其名曰不会卡牙齿缝,瘦肉就会卡。其实是肥肉里面的油脂别有一番风味,对于无油发酵的豆豉,如果给它点猪油的滋润,那简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妙不可言啊。
于是,豆豉回锅肉就应运而生。把猪五花肉洗干净煮几分钟,切片,准备姜葱蒜、干辣椒、豆豉适量。锅里放一点底油,爆炒五花肉,等五花肉出油了,边角翘起来,成为一个小窝窝一般,赶紧下姜蒜爆炒出香味,再下干辣椒段、干豆豉,瞬间猪油的香味和干豆豉的酱香融合了,这味道,上头得很,远飘出去,楼上楼下的相当于都得吃了,香。起锅前加点蒜苗叶子,味道和颜色搭配更棒。出锅以后,干豆豉不再像从小煤窑里面出来的干瘦黑,而是过上了富裕生活,披上了油亮亮的外衣,和五花肉这个大款打成一片,其乐融融,我们吃得那叫一个带劲,美滋滋。
豆豉蒸鱼,一般用的是黑豆发的豆豉,有豆豉去腥味,提升鱼肉鲜香,黑色豆和白色鱼肉颜色搭配也很赏心悦目。
豆豉炒油炸,一般不用熬好的猪板油和花油油炸,母亲说,猪板油熬的油炸太碎了,不脆;花油熬的油炸不够香,最好的油渣还得是猪肥肉熬出来的油渣,做法和炒豆豉回锅肉差不多,注意火候不能太大。
豆豉约创制于春秋、战国之际。《楚辞·招魂》载有“大苦咸酸”,根据注释,“大苦”即豆豉。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秦文献无豆豉,当是秦汉之际出现。《史记·货殖列传》始见豆豉记述。《齐民要术》有制作豆豉的技法。东汉开始用作药物。以后历代食籍、药籍均有关于豆豉的记述。至今仍为重要调味料之一。豆豉古称幽菽,唐代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古今流传。传说王勃在为滕王阁作序的时候,与中药豆豉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说到豆豉,现代人还会联想到日本的纳豆。纳豆和豆豉虽然在制作原料上都是大豆,但它们并不相同,纳豆源于中国,发酵好以后也是臭不可闻,纳豆类似中国的发酵豆、怪味豆。古书记载有:“纳豆自中国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纳豆初始于中国的豆豉。纳豆不含盐,但是含有一种酶,叫纳豆激酶。据说,这纳豆激酶使日本人平均寿命增长了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