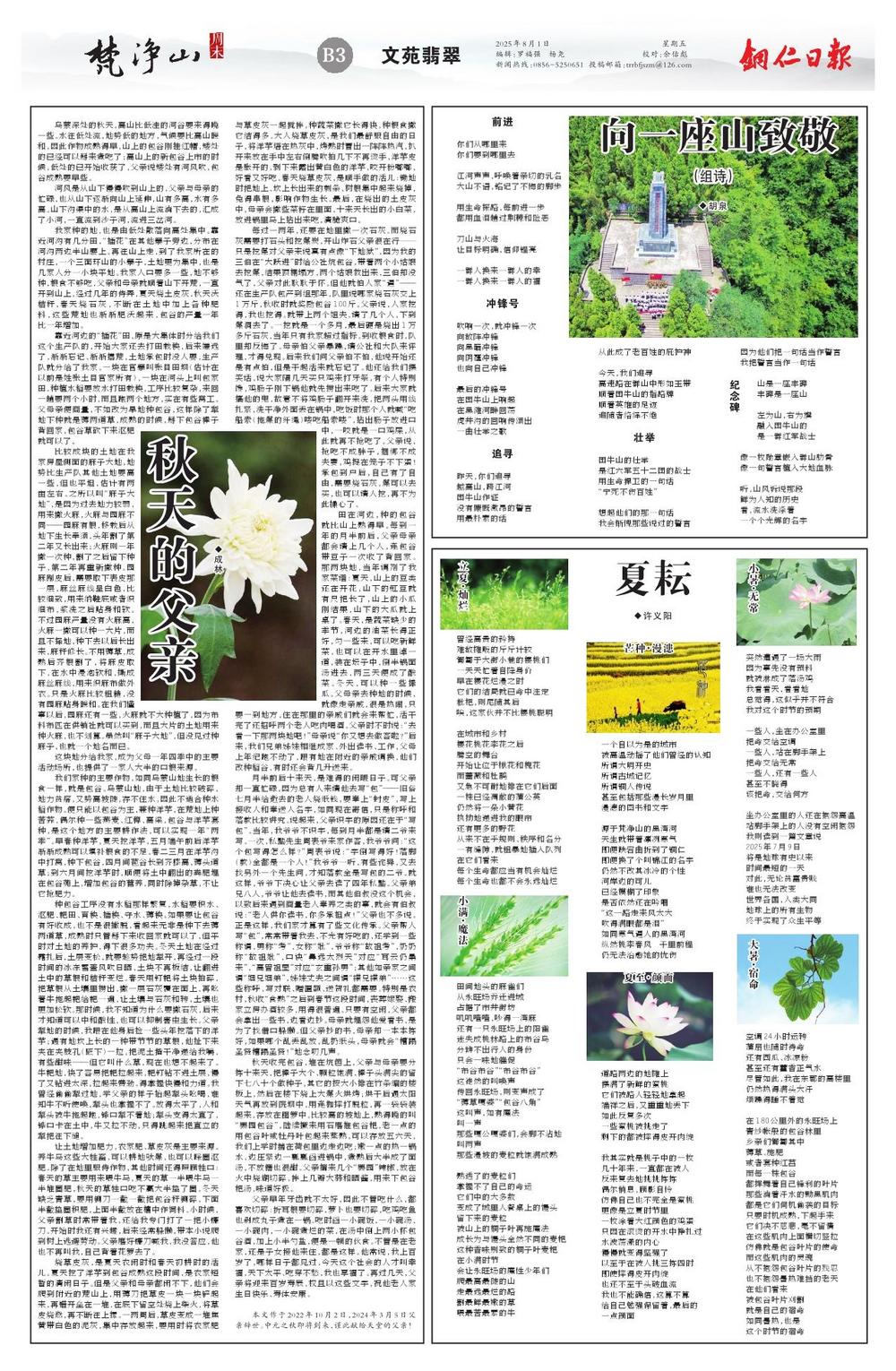乌蒙深处的秋天,高山比低洼的河谷要来得晚一些。水往低处流,地势低的地方,气候要比高山暖和,因此作物成熟得早,山上的包谷刚挂红帽,矮处的已经可以掰来煮吃了;高山上的新包谷上市的时候,低处的已开始收获了,父亲说矮处有河风吹,包谷成熟要早些。
河风是从山下慢慢吹到山上的,父亲与母亲的忙碌,也从山下逐渐向山上延伸,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下沟渠中的水,是从高山上流淌下去的,汇成了小河,一直流到沙子河,流进三岔河。
我家种的地,也是由低处散落向高处集中。靠近河沟有几分田,“插花”在其他寨子旁边,分布在河沟两边半山腰上。再往山上走,到了我家所在的村庄,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寨子,土地更为集中,也是几家人分一小块平地。我家人口要多一些,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父亲和母亲就顺着山下开荒,一直开到山上,经过几年的侍弄,夏天烧土皮灰,秋天沃秸秆,春天烧石灰,不断在土地中加上各种肥料,这些荒地也渐渐肥沃起来,包谷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靠近河边的“插花”田,原是大集体时分给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开始大家还去打田栽秧,后来嫌远了,渐渐忘记、渐渐撂荒,土地承包时没人要,生产队就分给了我家。一块在官寨叫张目田坝(估计在以前是姓张土目官家所有),一块在河头上叫包家田。种植水稻要放水打田栽秧,工序比较复杂,来回一趟要两个小时,而且跑两个地方,实在有些窝工。父母亲便商量,不如改为旱地种包谷,这样除了犁地下种就是薅两道草,成熟的时候,掰下包谷棒子背回家,包谷草砍下来沤肥就可以了。
比较成块的土地在我家房屋侧面的麻子大地,地势比生产队其他土地要高一些,但也平坦,估计有两亩左右。之所以叫“麻子大地”,是因为过去地力较弱,用来撒火麻,火麻与园麻不同——园麻有根,移栽后从地下生长牵须,头年割了第二年又长出来;火麻则一年撒一次种,割了之后留下种子,第二年再重新撒种。园麻剐皮后,需要取下表皮那一层,麻丝麻线呈白色,比较细致,用来纳鞋底或者织细布,浆洗之后贴身和软。不过园麻产量没有火麻高,火麻一撒可以种一大片,而且不择地,种下去以后长出来,麻秆修长。不用薅草,成熟后齐根割了,将麻皮取下,在水中浸泡软和,撕成麻丝麻线,用来织麻布做外衣。只是火麻比较粗糙,没有园麻贴身暖和。在我们懂事以后,园麻还有一些,火麻就不大种植了,因为布料布匹在供销社就可以买到,而且大片的土地用来种火麻,也不划算。虽然叫“麻子大地”,但没见过种麻子,也就一个地名而已。
这块地分给我家,成为父母一年四季中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提供了一家人大半的口粮来源。
我们家种的主要作物,如同乌蒙山地生长的粮食一样,就是包谷。乌蒙山地,由于土地比较破碎,地力贫瘠,又势高坡陡,存不住水,因此不适合种水稻作物。便只能以包谷为主,兼种洋芋,在荒地上种苦荞,偶尔种一些燕麦、红稗、高粱,包谷与洋芋套种,是这个地方的主要耕作法,可以实现一年“两季”。早春种洋芋,夏天挖洋芋,五月端午前后洋芋渐渐成熟可以填补粮食的不足。春二三月在洋芋沟中打窝,种下包谷,四月间苞谷长到齐膝高,薅头道草;到六月间挖洋芋时,顺便将土中翻出的粪肥埋在包谷蔸上,增加包谷的营养,同时除掉杂草,不让它抢肥力。
种包谷工序没有水稻那样繁复,水稻要积水、沤肥、耙田、育秧、插秧、守水、薅秧。如果要让包谷有好收成,也不是很撇脱,看起来无非是种下去薅两道草,成熟时只管掰下来收回家就可以了,但平时对土地的养护,得下很多功夫。冬天土地在经过霜扎后,土层变松,就要趁势把地犁开,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冰冻雪盖风吹日晒,土块不再板结,让翻进土中的草根和秸秆变烂。春天用钉耙将土块拍碎,把草根从土壤里捞出,撒一层石灰覆在面上,再吆着牛拖起耙给耙一遍,让土壤与石灰和转,土壤也更加松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撒石灰,后来才知道可以中和酸性,也可以抑制害虫生长。父亲犁地的时候,我跟在他身后捡一些头年挖落下的洋芋;遇有地坎上长的一种带节节的草根,他扯下来夹在夹肢孔(腋下)一拉,把泥土揩干净递给我嚼,有些甜味——但它叫什么草,现在也想不起来了。牛耙地,快了容易把耙拉起来,耙钉钻不进土层,慢了又钻进太深,拉起来费劲。得掌握快慢和力道。我曾经偷偷犁过地,学父亲的样子抬起犁头吆喝,谁知牛不听使唤,犁头也掌握不了。放得太平了,人和犁头被牛拖起跑,铧口犁不着地;犁头支得太直了,铧口卡在土中,牛又拉不动,只得跳起来把直立的犁把往下缒。
让土地增加肥力,农家肥、草皮灰是主要来源。养牛马这些大牲畜,可以耕地驮煤,也可以踩圈沤肥。除了在地里服侍作物,其他时间还得照顾牲口:春天的草主要用来喂牛马,夏天的草一半喂牛马一半堆圈肥,秋天的草牲口吃不赢大半垫了圈。冬天缺乏青草,要用铡刀一截一截把包谷秆铡碎,下面半截垫圈积肥,上面半截放在槽中作饲料。小时候,父亲割草时常带着我,还给我专门打了一把小镰刀。开始时我还有兴趣,后来经常躲懒,带本小说爬到树上逃避劳动。父亲磨好镰刀喊我,我没答应,他也不再叫我,自己背着花箩去了。
烧草皮灰,是夏天农闲时和春天初耕时的活儿。夏天挖了洋芋到包谷成熟这段时间,是农家短暂的清闲日子。但是父亲和母亲都闲不下,他们会爬到附近的荒山上,用薅刀把草皮一块一块铲起来,再错开垒在一堆,在底下留空处烧上柴火,将草皮烧燃,再不断往上摞。一两周后,草皮变成一堆焦黄带白色的泥灰,集中存放起来,要用时将农家肥与草皮灰一起搅拌,种蔬菜撒它长得快,种粮食撒它结得多。大人烧草皮灰,是我们最舒服自由的日子,将洋芋焐在热灰中,烤熟时冒出一阵阵热汽,扒开来放在手中左右倒腾吹拍几下不再烫手,洋芋皮是胀开的,剥下来露出黄白色的洋芋,咬开粉嘟嘟,好看又好吃。春天烧草皮灰,是顺手做的活儿:锄地时把地上、坎上长出来的刺条、树根集中起来烧掉,免得串根,影响作物生长。最后,在烧出的土皮灰中,母亲会撒些菜籽在里面,十来天长出的小白菜,放进锅里马上拈出来吃,清脆爽口。
每过一两年,还要在地里撒一次石灰。而烧石灰需要打石头和挖煤炭,开山炸石父亲很在行——只是挖煤对父亲来说真有点像“下地狱”,因为我的三伯在“大跃进”时给公社炕包谷,带着两个小姑娘去挖煤,结果顶棚塌方,两个姑娘救出来,三伯却没气了,父亲对此耿耿于怀。但他就怕人家“逼”——还在生产队包产到组那年,队里说哪家烧石灰交上1万斤,秋收时就奖励包谷100斤。父亲说,人家挖得,我也挖得。就带上两个姐夫,请了几个人,下到煤洞去了。一挖就是一个多月,最后硬是烧出1万多斤石灰,当年只有我家超过指标。到收粮食时,队里却反悔了。母亲怕父亲暴躁,请公社和大队来评理,才得兑现。后来我们问父亲怕不怕,他说开始还是有点怕,但是干起活来就忘记了。他还给我们摆笑话,说大家隔几天买只鸡来打牙祭,有个人特别馋,鸡肠子刚下锅他就先捞出来吃了。后来大家就搞他的鬼,故意不将鸡肠子翻开来洗,把两头用线扎紧,洗干净外面丢在锅中,吃饭时那个人就喊“吃船索(拖煤的纤绳)喽吃船索喽”,拈出肠子放进口中,一咬就是一口鸡屎,从此就再不抢吃了。父亲说,抢吃不成胖子,捆绑不成夫妻,鸡捉在笼子不下蛋!承包到户后,自己有了自由,需要烧石灰,煤可以去买,也可以请人挖,再不为此操心了。
田在河边,种的包谷就比山上熟得早。每到一年的月半前后,父亲母亲都会请上几个人,连包谷带豆子一次收了背回家。那两块地,当年调剂了我家菜谱:夏天,山上的豆类还在开花,山下的豇豆就有尺把长了,山上的小瓜刚结果,山下的大瓜就上桌了。春天,是蔬菜缺少的季节,河边的油菜长得正好,匀一些来,可以吃新鲜菜,也可以在开水里淖一道,装在坛子中,倒半锅面汤进去,两三天便成了酸菜。冬天,可以种一些捧瓜。父母亲去种地的时候,就像走亲戚,很是热闹,只要一到地方,住在那里的亲戚们就会来帮忙,活干完了还招呼两个老人吃肉喝酒。父亲时不时说:“去看一下那两块地吧!”母亲说“你又想去做客啦?”后来,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成家、外出读书、工作,父母上年纪跑不动了,跟有地在附近的亲戚调换,他们改种稻谷,有时还会背几升送来。
月半前后十来天,是难得的闲暇日子。可父亲却一直忙碌,因为总有人来请他去写“包”——旧俗七月半给逝去的老人烧纸钱,要奉上“封皮”,写上接收人和奉送人名字,如同现在寄信,只是称呼和落款比较讲究。说起来,父亲识字的原因还在于“写包”。当年,我爷爷不识字,每到月半都是请二爷来写。一次,私塾先生周表爷来家作客,我爷爷问:“这个包写得怎么样?”周表爷说:“字倒写得好!落脚(款)全都是一个人!”我爷爷一听,有些诧异,又去找另外一个先生问,才知落款全是写包的二爷。就这样,爷爷下决心让父亲去读了四年私塾。父亲弟兄八人,爷爷让他去读书,而其他伯叔没这个机会,以致后来遇到商量老人奉养之类的事,就会有伯叔说:“老人供你读书,你多承担点!”父亲也不多说。正是这样,我们家才算有了些文化传承。父亲帮人写“包”,常常带着我去,不光有好吃的,还学到一些称谓,男称“考”,女称“妣”,爷爷称“故祖考”,奶奶称“故祖妣”,口诀“鼻远太烈天”对应“耳云仍晜来”,“高曾祖显”对应“玄重孙男”;其他如亲家之间谓“姻兄姻弟”,姊妹丈夫之间谓“襟兄襟弟”……这些称呼,写对联、赠匾额、送贺礼都需要。特别是农村,秋收“食熟”之后到春节这段时间,丧葬嫁娶、搬家立房办酒较多,用得很普遍。只要有空闲,父亲都会拿出一些书,边看边抄。母亲就埋怨他爱看书,是为了找借口躲懒。但父亲抄的书,母亲却一本本拣好,如果哪个乱丢乱放,乱扔纸头,母亲就会“糟蹋圣贤糟蹋圣贤!”地念叨几声。
秋天收完包谷,堆在炕笆上,父亲与母亲要分拣十来天,把棒子大个、颗粒饱满、棒子头满尖的留下七八十个做种子,其它的按大小排在竹条编的楼板上,然后在楼下烧上大煤火烘烤;烘干后遇太阳天气再放到院坝中,用连枷摔打脱粒,再一袋袋装起来,存放在囤箩中。比较高的坡地上,熟得晚的叫“罢园包谷”,陆续撅来用石磨推包谷粑,老一点的用包谷叶或牡丹叶包起来蒸熟,可以存放五六天,我们上学时揣在荷包里边走边吃;嫩一点的热一锅水,边压紧边一瓢瓢舀进锅中,煮熟后大半成了面汤,不放糖也很甜。父亲摘来几个“罢园”辣椒,放在火中烧煳切碎,拌上几瓣大蒜和晒酱,用来下包谷粑汤,味道好极。
父亲早年牙齿就不太好,因此不管吃什么,都喜欢切碎:折耳根要切碎,萝卜也要切碎,吃鸡吃鱼也剁成丸子煮在一锅。吃时舀一小碗饭,一小碗汤,一小碗肉,一小碗煮烂的菜,在汤中倒上两小杯包谷酒,加上小半勺盐,便是一顿的伙食。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子女接他来住,都是这样。他常说,我上百岁了,哪样日子都见过,今天这个社会的人才叫幸福,天下太平、吃穿不愁,我也享福了。再过几天,父亲将迎来百岁寿辰,权且以这些文字,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寿体安康。
本文作于2022年10月2日,2024年3月5日父亲辞世。中元之秋即将到来,谨此献给天堂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