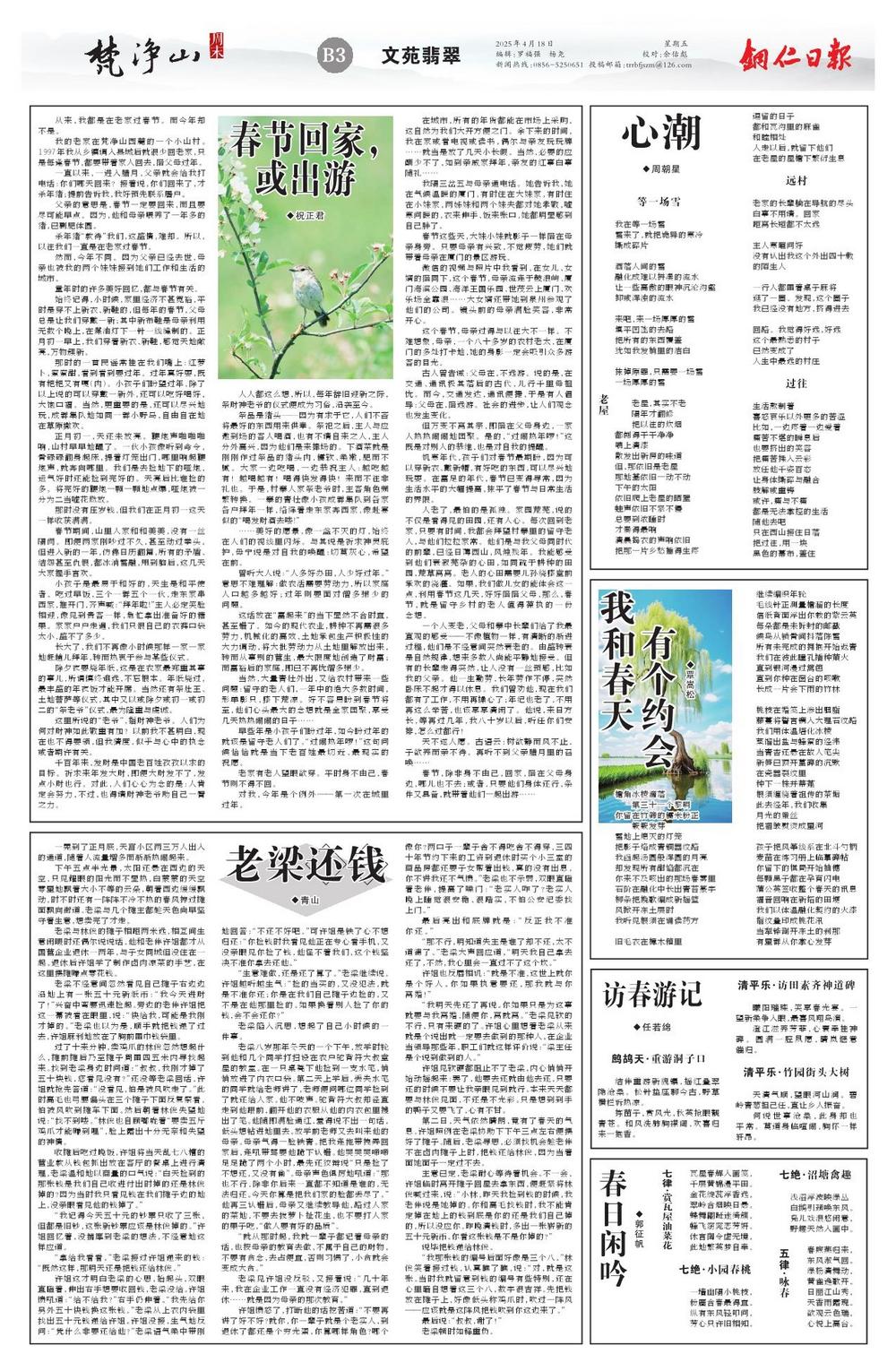从来,我都是在老家过春节。而今年却不是。
我的老家在梵净山西麓的一个小山村。1997年我从乡镇调入县城后就很少回老家,只是每逢春节,都要带着家人回去,陪父母过年。
一直以来,一进入腊月,父亲就会给我打电话:你们哪天回来?接着说,你们回来了,才杀年猪;提前告诉我,我好预先联系屠户。
父亲的意思是,春节一定要回来,而且要尽可能早点。因为,他和母亲喂养了一年多的猪,已剽肥体圆。
杀年猪“款待”我们,这盛情,难却。所以,以往我们一直是在老家过春节。
然而,今年不同。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被我的两个妹妹接到她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童年时的许多美好回忆,都与春节有关。
始终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不甚宽裕,平时是穿不上新衣、新鞋的,但每年的春节,父母总是让我们穿戴一新;其中新布鞋是母亲利用无数个晚上,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正月初一早上,我们穿着新衣、新鞋,感觉天地敞亮,万物簇新。
那时的一首民谣常挂在我们嘴上: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过年真好耍,既有粑粑又有嘎(肉)。小孩子们盼望过年,除了以上说的可以穿戴一新外,还可以吃好喝好,大饱口福。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尽兴地玩,成群集队地如同一群小野马,自由自在地在草原撒欢。
正月初一,天还未放亮。鞭炮声啪啪啪响,山村早早地醒了。一伙小孩像听到命令,骨碌碌翻身起床,提着灯笼出门,哪里响起鞭炮声,就奔向哪里。我们是去捡地下的哑炮,运气好时还能捡到完好的。天亮后比谁捡的多。将完好的鞭炮一颗一颗地点爆,哑炮被一分为二当嘘花燃放。
那时没有压岁钱,但我们在正月初一这天一样收获满满。
春节期间,山里人家和和美美,没有一丝隔阂。即便两家刚吵过不久,甚至动过拳头,但进入新的一年,仿佛日历翻篇,所有的矛盾、结怨甚至仇恨,都冰消雪融,甩到脑后,这几天大家握手言欢。
小孩子是最易于和好的,天生是和平使者。吃过早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走东家串西家,推开门,齐声喊:“拜年啦!”主人必定笑脸相迎,像见到贵客一样,急忙拿出准备好的糖果。家家户户走遍,我们只恨自己的衣裤口袋太小,盛不了多少。
长大了,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一家一家地赶趟儿拜年,转而热衷于参与某些仪式。
除夕夜要烧年纸,这是在农家最郑重其事的事儿,所谓慎终追远,不忘根本。年纸烧过,最丰盛的年夜饭才能开席。当然还有祭灶王、土地菩萨等仪式,其中又以或除夕或初一或初二的“祭老爷”仪式,最为隆重与虔诚。
这里所说的“老爷”,指财神老爷。人们为何对财神如此敬重有加?以前我不甚明白,现在也不得要领,但我猜度,似乎与心中的执念或者期许有关。
千百年来,发财是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目标。祈求来年发大财,即便大财发不了,发点小财也行。对此,人们心心为念的是:人肯定会努力,不过,也得请财神老爷助自己一臂之力。
人人都这么想,所以,每年辞旧迎新之际,祭财神老爷的仪式便成为习俗,沿袭至今。
祭品是猪头——因为有求于它,人们不吝将最好的东西用来供奉。祭祀之后,主人与应邀到场的客人喝酒,也有不请自来之人,主人分外高兴,因为他们是来捧场的。下酒菜就是刚刚作过祭品的猪头肉,糯软、柔嫩,肥而不腻。大家一边吃喝,一边恭祝主人:越吃越有!越喝越有!喝得快发得快!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村寨人家祭老爷时,主客角色频繁转换。一寨的青壮像小孩成群集队到各家各户拜年一样,络绎着走东家奔西家,像赴宴似的“喝发财酒去喽!”
……美好的愿景,像一盏不灭的灯,始终在人们的视线里闪烁。与其说是祈求神灵庇护,毋宁说是对自我的唤醒:切莫灰心,希望在前。
曾听大人说:“人多好办田,人少好过年。”意思不难理解:做农活需要劳动力,所以家庭人口越多越好;过年则要面对僧多粥少的问题。
这话放在“富起来”的当下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错了。如今的现代农业,耕种不再需很多劳力,机械化的高效,土地承包生产积极性的大力调动,将大批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转而从事别的营生,最大限度地创造了财富;而富裕后的家庭,即已不再忧僧多粥少。
当然,大量青壮外出,又给农村带来一些问题:留守的老人们,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形单影只,膝下荒凉。好不容易盼到春节将至,他们心头最大的念想就是全家团聚,享受几天热热闹闹的日子……
早些年是小孩子们盼过年,如今盼过年的就该是留守老人们了。“过闹热年啰!”这句问候恰恰就是当下老百姓最切近、最现实的祝愿。
老家有老人望眼欲穿。平时身不由己,春节则不得不回。
对我,今年是个例外——第一次在城里过年。
在城市,所有的年货都能在市场上采购,这自然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余下来的时间,我在家或看电视或读书,偶尔与亲友玩玩牌……就当是放了几天小长假。当然,必要的应酬少不了,如到亲戚家拜年,亲友的红事白事随礼……
我隔三岔五与母亲通电话。她告诉我,她在气候温暖的厦门,有时住在大妹家,有时住在小妹家,两姊妹和两个妹夫都对她孝敬,嘘寒问暖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她都明显感到自己胖了。
春节这些天,大妹小妹就影子一样陪在母亲身旁。只要母亲有兴致,不觉疲劳,她们就带着母亲在厦门的景区游玩。
微信的视频与照片中我看到,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这个春节,母亲流连于鼓浪屿、厦门海滨公园、海洋王国乐园、世茂云上厦门、欢乐场全靠浪……大女婿还带她到泉州参观了他们的公司。镜头前的母亲满脸笑容,非常开心。
这个春节,母亲过得与以往大不一样。不难想象,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在厦门的多处打卡地,她的身影一定会吸引众多游客的目光。
古人曾告诫:父母在,不远游。说的是,在交通、通讯极其落后的古代,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今,交通发达,通讯便捷,于是有人倡导:父母在,陪远游。社会的进步,让人们观念也发生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即陪在父母身边,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团聚。是的,“过闹热年啰!”这既是对别人的恭维,也是对自我的提醒。
饥寒年代,孩子们对春节最期盼,因为可以穿新衣、戴新帽,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尽兴地玩耍。在富足的年代,春节已变得寻常,因为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抹平了春节与日常生活的界限。
人老了,最怕的是孤独。家园荒芜,说的不仅是看得见的田园,还有人心。每次回到老家,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拜望村寨里的留守老人,与他们拉拉家常。他们是与我父母同时代的前辈,已经日薄西山,风烛残年。我能感受到他们衰寂芜杂的心田,如同疏于耕种的田园,荒草离离。老人的心田需要儿孙绕膝堂前承欢的浇灌。如果,我们做儿女的能体会这一点,利用春节这几天,好好陪陪父母,那么,春节,就是留守乡村的老人值得葆执的一份念想。
一个人变老,父母和寨中长辈们给了我最直观的感受——不像植物一样,有清晰的渐进过程,他们是不经意间突然衰老的。由盛转衰是自然规律,想来多数人尚能平静地接受。但有的长辈走得突然,让人没有一丝预感,比如我的父亲。他一生勤劳,长年劳作不停,突然卧床不起才得以休息。我们曾劝他,现在我们都有了工作,不用再操心了;年纪也老了,不用再这么辛苦,也该享享清闲了。他说,来日方长,等再过几年,我八十岁以后,听任你们安排,怎么过都行!
天不遂人愿。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再听不到父亲腊月里的召唤……
春节,除非身不由己,回家,陪在父母身边,哪儿也不去;或者,只要他们身体还行,条件又具备,就带着他们一起出游……